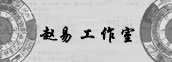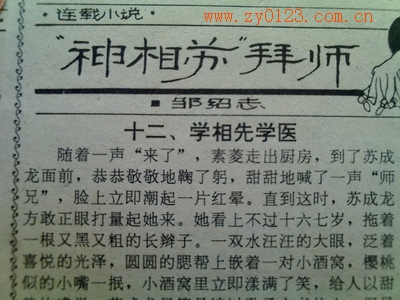林希(诗人) 著 原载(《中国作家》1990年第2期) 中国看相大师 六爻卜卦 上海风水 预测师 风水大师 奇门大师 趙易 上海起名 起名 起名大师 算命先生 地产风水 桐庐风水 山水别墅风水 镇江风水大师 台湾风水大师 香港风水大师 苏州风水 镇江起名大师 酒店风水 玄空风水大师 风水教授楼盘取名趙易整理
上接>>>《相士无非子》(中)
七、
哈哈王爷不识地舆图,至今每看见地舆图总要哈哈笑。刘洞门认真地将一张地舆图社印制的大地图铺在案上赵易,可着性地胡弄哈哈王爷,他将大拇指按在一个地方zy0123,指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对哈哈王爷说img2.tbcdn.cn/tfscom/T11oGPFhVdXXXtxVjX.swf:“这儿就是柴猪堡。”
“我不管什么柴猪堡,柴狗堡,我家祖坟在四子王。”
“这儿,就是四子王赵易。”刘洞门按在地舆图上的大拇指未动,随即伸出食指,巴叉开手往远处伸去,食指按的地方,就是哈哈王爷家的老祖坟。
“这么近?”哈哈王爷支楞从太师椅上站起来,双手按在条案上,俯下身去看地舆图。
“所以传言奉军威胁你府上祖坟,不是没有根据。”刘洞门见哈哈王爷吓呆了,这才将手掌抽回来,对哈哈王爷仔细述说,“早以先,阎锡山的一个军长守在柴猪堡,十几年没动你家祖坟……”
“他仁义。”哈哈王爷赞叹着,“我当早送他一份厚礼。”
“如今这军长被奉系军长打跑了……”
“这就是奉系军人的不对,人家的地盘,你凭白无故地抢过来,没道理。”哈哈王爷主持公道,自然对世事有个评议。
“为什么要作没道理的事?”刘洞门问着。
“因为他不讲理。”哈哈王爷回答。
“他贪图那地界之内的金银财宝,地上的金银财宝,地下的金银财宝。”
“啊!”哈哈王爷紧张地吸一口长气。
“知道孙大麻子掘老佛爷皇陵的事吗?”刘洞门凌厉的双目直视着哈哈王爷质问。
哈哈王爷打了个寒战,孙殿英掘慈禧墓的事太可怕了,不光盗走了全部下葬的金银财宝,还将老祖宗剥光了衣眼仰面朝天抛在了棺材板上,溥仪和北洋政府打了一场官司,才重新将慈禧的尸体收殓下葬。
“赶紧给我将阎锡山的那个老军长找回来,给他钱让他招兵买马把那个什么堡收回来,就算是我买个洋枪队护卫祖宗坟茔。列祖列宗在上,不是子孙不孝,是这世道太坏了呀,人人都惦着掘人家祖坟,这些断子绝孙的强盗zy0123!皇上退位,江山易主,老朽我死皮赖脸还活在世上,为的就是为祖宗看守这一处坟茔,倘我家祖坟有个不测的灾殃,老朽我还活着作嘛呀!”说着,哈哈王爷声泪俱下,他似看到了自家祖坟被掘的惨象,他家祖辈是和摄政工一道进关的,皇上死了下葬时有啥,他德王爷祖上死后下葬时也有啥,他家的祖坟顶得上一个大金矿呀!哈哈王爷再不敢哈哈了。
刘洞门见哈哈王爷已经咬钩,便婉言告辞出来,找小神仙设法往聚合成为无非子送信。
……
无非子在聚合成饭庄被袁军长已经囚了七八天了,这一些日子袁军长四处碰壁,筹措军款招兵买马的事连个影儿都没有,这年月英雄豪杰遍地皆是,正在春风得意之时的好汉还愁拜不上门子呢,累累若丧家之犬的袁军长去哪里投靠山?
袁军长白天东奔西跑,晚上垂头丧气地回来,每日后半夜他便来到无非子的客房,和无非子扯闲篇拉闲嗑。
“都怪我这人莽撞。”想起吃败仗的往事,袁军长万般悔恨地说着,“人家都劝我应该在军部养一位术士,不是俺只相信自己火力旺,是俺怕阎锡山疑心我要自立炉灶,阎锡山心胸狭窄,有人说他的肚量如同汾河湾,又细又浅又弯弯绕,倘若我养了术士,他非得除了我不成。早若是有神仙这样的相士在我身边,何至于我落到这步田地?”
“胜败乃兵家常事。”无非子劝解他说。
“可是没有似我败到这等份儿上的,让人家来个扫地出门,事后我才知道是上了当,那姓荣的本来是为张大胡子阅兵去的,是从我境内借路……”
无非子听着不置可否,只自言自语地沉吟道:“兵者,诡道也。《孙子》讲用兵之道,至理名言。兵家借路过境,其用心也恶,未必不怀诡计,何况袁军长久据柴猪堡,自然是刚愎自用,如此荣军长便故意在你眼里揉砂子,激之令怒,袁军长便不顾本谋了。”
“神仙,你是活神仙!”袁军长站起身来,举起右手向无非子敬了一个军礼,“活神仙你跟我走吧,我明里作军长,你暗里作军长,用兵动武我全听你的,你叫我进我就进,你让我守我就守,你让俺打哪一个,俺就打哪一个,神仙给我作诸葛亮吧。”
“无非子不出山、不下海,只坐在相室里不出山门一步。”无非子语音平和地说。
“唉!”袁军长深深地叹息着,“我信了神仙断给我的一个‘进’字,这许多日我四处联络,连一点门路都没找到,我不疑惑神仙的话不灵验,必是我的时运还没到时辰。反正这些日我也没事,神仙细细地给我批一卦吧。我听说神仙批一卦是两千元,如今我是穷光蛋呀,等来日我时来运转,我高高地给神仙送上二十万。”
无非子也是闲得睡不着觉,便在座椅上正襟危坐地端好架势,微微合上眼睛说道:“好吧,这一卦我分文不取,只算我交个朋友。”
“也算我识位真人。”袁军长也规规矩矩坐好,等着由无非子批示命相。
“拿纸笔来。”无非子一声吩咐,早有人送上来宣纸笔砚。无非子将宣纸铺好,娴熟地只不多时间便画成了一幅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,随之他便将两手在六十四卦图上比来比去,无非子将袁军长的命相断清了。
“神仙有话直说。”袁军长万般虔诚地等着。
“先甲三日,后甲三日。”无非子只顾自己说着,似是对面压根儿没有袁军长一般。“先甲三日,幸也,前事过中而将坏,则可自新以为后事之端。初二二上,九五,兑下坤上,有贵人,三日至。”
“有贵人?”袁军长欠着屁股半站起身来,“是贵人来找我,还是我去找贵人。”袁军长急切地追问。
无非子根本不理睬袁军长的询问,只管自己睡觉去了。
“报告。”无非子刚走,有人就悄声禀报袁军长,“一位老王爷求见。”
“放你妈个屁!”袁军长一口唾沫吐在地上,“天还没亮呢,他见我干嘛?看好了,别是张大胡子派下的刺客!”
“报告军长,小的盘问过,他说有要事,只能对军长一个人说。”
“我不见!”袁军长狠狠地将房门摔上。
只是那个副官忠于职守,他万般柔顺地推门进来,俯身在袁军长耳边嚓嚓嘁嘁地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,最后只见袁军长腾地迈开大步,随着副官往外走,一面走着还一面唠叨:“会有这种事?邪门儿。”
……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约莫着到了中午,袁军长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无非子的客房,他将上衣脱下来信手抛在沙发椅上,然后开怀大笑着对无非子说着:“神仙真灵,你说三日内不出门户必有贵人,天还没亮,贵人就找上门来了。一位德王爷,拿他的开平煤矿股票作押,给我在大通借了一笔款,百多十万,指名让我招兵买马收复失地。王爷有约法,这笔款只能买军火,只能作军款,不许我吃喝玩乐,收复柴猪堡之后立即还清。你说也怪,这个王爷干嘛非要我去收回那片地盘?他说那地界里有他家祖坟,驻守这许多年,我咋不知道?人说凡是王爷府的祖坟里都有国宝,等收复柴猪堡我还真得找找这块宝地。你瞧瞧,我早认准只要下天津卫必能找到一条活路,这地方藏龙卧虎,谁不想找个好汉为他打天下呀?没说的,柴猪堡也好大一片地势,他王爷不是惦着作皇上吗?等有了地盘,俺给他立个号,照着宫殿的样儿给他盖个宅院,每日也给他演习上朝下朝的典礼。谁爱玩什么就由他玩什么好了,干嘛非得按着一个法儿,弄得人人别别扭扭老大不高兴。段祺瑞愿意作总理,由他设总理衙门;袁大头想作皇帝,随着他自封是洪宪;黎元洪愿意当大总统,孙传芳喜欢作联军司令,谁说自己是啥,谁就是啥,共和嘛,一共二和,不共不和就过不上好日月。神仙,你说说我这些话够不够个胡博士?别以为我是粗人,我敬重念书人,凡是完全两级小学毕业的,在我那儿起码是县长,若是胡博士肯去柴猪堡,俺给他盖圣人府。”说到得意处,袁军长喜笑颜开,如今他筹措到了军款,用不了多久他又能回柴猪堡作他的地头蛇去了。“我已经下了命令,打道回府,这一层楼房我还包着,还得留几位副官和银号打交道,还要和洋行买军火,我得走,我要去带兵打仗。神仙哩,你还得住在这里,几时捷报传来,我又收复下柴猪堡了,这儿的人便几时护送神仙回相室。不是我和神仙为难,谁让你这样灵呢,我怕你再去给别人算命相面,说不定张胡子要找你,给他批批命相,这柴猪堡守得住守不住呀?神仙知道我的底,再去给他批八字,我又让你们玩儿了。万一攻不下柴猪堡咋办哩?那时王爷担保借我的钱也花光了,阎锡山更恨得我咬牙切齿,张胡子的人也不肯放过我。那时我再回来找神仙,我一根绳儿,神仙一根绳儿,咱两个脸冲着脸地就吊在这屋里。我哩,算是个脓包无能,神仙哩,算是说话不灵,咱两个就都别在这世上蒙人了。”
袁军长露出一副流氓相,直到现在他还觉得这事太奇巧,他怀疑是无非子要他,压根儿他就拿自己错当成张作霖的部下荣军长,一个“进”字说错了,才将错就错,顺水推舟,设个陷阱诱他往下跳。等着瞧吧,袁某人也不是好惹的,无非子自作自受,吃不了兜着走吧。
八、
扑籁籁,无非子流下了眼泪儿。
袁军长带着左膀右臂几员武夫走了,临走前无非子扎扎实实地给他算了一卦,这一卦算得他必须先奔西北,西北地界有几个师的兵力因找不到有奶的娘几乎已沦为流寇,只要带上钱到那里就能拉出兵马,保证袁军长麾下还能有精兵强将。至于围攻柴猪堡的时辰,无非子算得是在四十天之后,四十天之后的哪一天?批不出个准日子,有几个吉日可以供作选择,但还要根据军情而定,但四十天之内不可用兵,因为袁军长这一步流年运气,印堂着班超,光熙精舍如武王,自印堂至光熙还差四十天的光阴,一切要好自为之。对于无非子的批相,袁军长记在心头,此次出师不成功便成仁,一定要杀出威风。
聚合成饭庄这一层楼客房只留下十几个人,其中大多是文职,每日操办军款、军火,且和各派军阀势力时时调整关系,还为袁军长刺探情报。空荡荡一层楼房只住着十几个男人,来来往往的女宾却多达四五十人。花界女郎最讲义气,投靠到一家门下,不将这门这户吃穷吃败吃垮吃光,决不会三心二意再去寻找新欢。袁军长住在聚合成时,一批随员,卫士,呼啦啦一群汉子,花呼哨一帮女流。如今大多数汉子走了,女流却没有减少,几个女宾包围一个好汉,如此就没有人顾得无非子了。
宋四妹这时才来到聚合成饭庄和无非子相会,一番卿卿我我之后,无非子对自己的相好吐露了真情。
“人生在世,成败本来无足轻重,有盛便有衰,有圆便有缺,有盈便有亏,四大皆空,宇宙本只一个无字。”无非子自我宽慰地感叹着,“只是我不该衰得这样早,也不该败得这样惨,我还没有给你挣下一笔产业,鬼谷生日后还要打着我的幌子混事由,我一败涂地,他如何问江湖呀!”
无非子虽然一番花言巧语将混星子袁军长说得天晕地转,又一番巧安排将哈哈王爷推进陷阱,终于保全下了自己一条性命;但他深知,袁军长尽管有了一笔巨款,但要想东山再起,也决非易事。张作霖本来不会久居关外,他好不容易调兵遣将在关内打出天下站稳脚跟,凭袁军长重新集结的一帮乌合之众也决不会再逼得张作霖让出山河。而正在得意之时的荣将军,已是越打越胜,越胜越勇,兵家贵在一个“威”字,四面楚歌,风声鹤唳尚且能击溃于军万马,如今只要凭借荣军长的大旗就足以令人闻风丧胆;袁军长卷土重来不过是鸡蛋碰石头,最后必是粉身碎骨,死无葬身之地。
“现如今是顾不得那许多了,总得想个办法逃出袁军长的监禁呀!”宋四妹对无非子一片真情胜过扎髻夫妻,无非子叹息她陪着抽泣,无非子掉眼泪她陪着哭鼻子。
“袁军长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聚合成饭庄包下房子设兵部,他就能买下黑道上的人置我于死地。不是我不能跑,在天津卫混这么多年,家家饭庄旅舍的后门地道我了如指掌,可是我溜出去容易,保活命难。这许多日子,倘我稍微流露出一点跑的意思,这聚合成后门就挨着海河,半夜三更将人装麻袋里沉到河底的事不是比扔根柴禾棍还容易了吗?”
“咱两人跑,上海有我的姐妹。”
“嘘!”无非子忙抬手捂住宋四妹的嘴巴。“你到了上海可以混,我呢?这江湖上吃子平饭,江南江北两不来往。”“子平”者也,就是江湖术士们对自身职业的称谓,如厨师称自己为勤行,胡编瞎掰的称自己为作家,招摇过市之徒称自己是明星一般。
“唉,那就真没活路了?”
宋四妹坐在床上双手托着腮,娇滴滴地歪着脑袋瞅着无非子,无非子看着宋四妹超凡的美貌面容,心中更觉自己的责任重大。
“一定要设法让袁军长收复柴猪堡,否则我休想逃出他的虎口。”无非子心事重重地说。
“逃出虎口之后,你更名改姓,我帮你做个小生意,这码头上不会饿死咱们的。”宋四妹一片真情,准备与无非子同舟共济一起过穷日子,而且还要作他的贤内助。
“不吃子平饭了?”无非子向宋四妹问道。
“谁还信你呀?将一个落魄武夫错看作是常胜将军,给一个吃了败仗的丧家犬批了个‘进’字,你还怎么好意思再设相室作相士?”宋四妹不无同情地对无非子说着。“那相室咱不要了,找个主儿兑出去,小神仙另起炉灶,换个名儿先去马路边上摆卦摊,求左十八爷成全着他,我再给他找几个‘敲托的’、‘贴靴的’。你没听说吗,南市刘半仙卦摊就常有一个披麻带孝的女人去哭拜,喊着叫着地说:‘神仙的卦真灵呀,昨日说孩儿的爹有飞来横祸,当晚就被电车轧死了。神仙再给我们孤儿寡母指条明路吧。’其实,那个哭喊的女人是他儿媳妇。嘻嘻。”宋四妹说到开心时,破涕为笑,笑得软软的身子八道弯儿。
“让我无非子从此销声匿迹,我还有点不甘心。唯能化险为夷者,方为大丈夫;欲扭转乾坤者,必先置于死地而后生,我一定要让袁军长收回柴猪堡!”说话时无非子用力地挥着拳头。
“你坐在这客房里,能有本领让袁军长收复失地?你若是道士行了,会妖术,坐在屋里一发妖术,千里万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;你一念咒,如今守柴猪堡的官兵就瘫成一堆烂泥,机关枪也不响了,装甲车也不转了,呆看着袁军长大摇大摆地坐收江山。”
“要想办法,要想办法。”无非子反背着手在客房里转来转去,他一双手用力地搓得咯咯响,两弯眉毛紧紧地锁成一条直线。
“你想办法吧,只要你能想出办法,我就去给你跑腿。”宋四妹一本正经地说着,“我这人也就这么点能耐。交际花嘛,能成全事。”
……
布翰林多日见不到无非子,心中郁郁不乐,每日下午他还是准时来无非子相室闲坐,盘问小神仙鬼谷生,问他师父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布翰林来找无非子,多年来只是研究学问,布翰林精于《易经》,写过一部《易经布注》,自己掏钱在扫叶山房活字版印了五百册,如今还堆在自家下房里没有拆包。无非子研究《易经》自成一家,两个人由史论易,由世论易,彼此谈得极是投机。老实讲,若不是为和无非子共同弘扬国粹,布翰林是不肯屈尊来无非子相室的。布翰林看不起哈哈王爷,正是这些草包王爷,直到自家亡了天下,还没闹明白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八国联军打进家门,还不相信世界上居然还有什么意大利、奥地利,布翰林将这等人看得如行尸走肉一般。对于刘洞门,布翰林更视若一介无赖,满嘴没有一句实话。倘若你看见他冲着一个人喊爹,你可千万别相信那个人是他的爸爸。一旦他发现被他唤作爹的人原来是个穷光蛋,立即一脚便将他远远踢开。至于那个左十八爷,布翰林从来不正眼看他,渣滓,非同类也。
偏偏无非子不见了踪影,布翰林觉得日月都没了光彩。
“听说你师父有个要好的女子,是不是两个人躲起来过荒唐岁月去了?”布翰林百无聊赖地问鬼谷生,一双眼睛还在相室里查看,看来看去果然不见有无非子的踪迹,这才想起了他素日不屑一提的女子。
“学生放肆。”未回答布翰林的询问,鬼谷生先向翰林施了一个拱手大礼,“子不敢言父,徒不敢言师,我师父此去一月有余,学生也是疑惑他必是故意躲避一桩什么事情。”
“这事倒是有的。”布翰林摇头摆脑地回答,“民国十三年二次直奉战争,吴佩孚自不量力要作中原霸主,其时冯玉祥将军已经率部入京,你师父料定吴佩孚必败。偏偏吴佩孚派下人来接你师父进京批命相面,为他看看武运造化,那一次你师父便躲了起来,对外放风说是老母去世回原籍守孝,其实是悄悄地住进了日租界。不如此何致干就结识了这位宋四小姐呢?直到吴佩孚大败远去江南,段祺瑞任执政大总统,你师父才又回到了相室。”
“翰林圣明。”鬼谷生诡诈地睨视着布翰林故意询问,“你说这次我师父躲谁呢?”
“躲孙传芳,孙传芳任五省联军司令,正在得意之时呀!”布翰林掐着指头自己默叨着,“躲张宗昌?张宗昌不到天津来,天津也没他的行馆。躲靳云鹏?靳总理有日本势力作后台,北洋各路好汉无论谁胜谁负都得捧着他当家主事。那,你说他躲谁呢?”
“学生不才,实在看不出什么门道。”鬼谷生要个滑头回避开布翰林的询问,趁布翰林闭目思忖的当儿,跑走开应酬门面去了。
没有无非子陪翰林说话,布翰林实在觉得无聊。可翰林不似无非子那另外的几个好友,不来无非子相室,还各有各的去处;布翰林除了在无非子相室闲坐之外,其它便再没有一个去处。大街上市声鼎沸,翰林乘包月车穿过街衢,犹如赴汤蹈火一般,坐在车里闭着眼睛,但满耳还是摩登女郎的笑声和商店收音机放出来的丧邦之音;逛商店,布翰林都叫不出那些洋货的名称,看着那些上百元一条的劳什子领带,看着那些伤风败俗的女人衣裙,布翰林只恨自己不该活到如今这一大把年纪,居然还要亲眼看到人变成了禽兽。此外,什么舞厅,真光电影院,弹子房、赛马场、回力球社,罪孽,罪孽,皇帝在位时,何以就没想到早把这类孽障除掉!
所以,尽管无非子相室不见了无非子,空空荡荡,相室里还坐着布翰林,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,翻阅相书,品味《易经》,喝茶,闻鼻烟,看报。无非子爱看报,相室里有许多报纸,什么《庸言》、《申报》、《民国》、《北洋》甚至还有《369画报》,以及许许多多没一篇正经文章的小报。布翰林看报是一目十行的,只有《庸言》报看得仔细,因为这《庸言》报的主笔是老熟人刘洞门,文若其人,报若其人,读《庸言》报就似当面听刘洞门说谎话一般。
不知为什么,这《庸言》报最近忽然对奉阎战局极是关注。头一版几乎全是奉阎战争的消息,什么专电、专稿,还有一幅一幅的大照片。读过这些天的报纸,布翰林得知一位袁大将军集结了数十万精兵,正浩浩荡荡地向奉军驻地调兵遣将。这位袁大将军得民心,所到之处民众列队欢迎慰劳,袁大将军的队伍纪律严明,一兵士因向小贩索要纸烟一支已被军法处判处当众重责四十军棍。而且袁大将军善用兵,是黄埔首届高材生,在德国研究军事多年,其关于战争学的专著已在英国出版,等等等等,看来,这位袁大将军马上就要成事了。
此事非同小可,布翰林放下报纸,悄悄地来到了春湖饭店。
春湖饭店是张作霖在天津的行馆,或者可以爱称是奉军的老窝。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,还有一个严密的特务体系,张作霖神不知鬼不觉地常来天津,来天津就住在春湖饭店,而这位布翰林,便是张大帅的一位密友。
张作霖立足东三省,脚踩两只船,一只船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。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觊觎东三省,对这一片沃土早就垂涎三尺,张作霖占据东三省,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得利益,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张作霖的后台老板。张作霖脚下踩的第二只船,是原来旗人势力的上层人物,因为关外毕竟是努尔哈赤的老家,而布翰林又是旗人势力上层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,高高地捧着布翰林,张作霖的江山就坐得稳当。对于张作霖的礼贤下士,布翰林是感恩戴德,中国读书人历来遵循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准则,所以暗中布翰林总给张作霖看着动静。
“翰林来得正好。”在春湖饭庄的密室里,布翰林见到了秘密潜来天津的张作霖,张大帅拉住布翰林,推心置腹地就要说知心话。
“大帅,我正有要事找你。”布翰林风风火火地坐在大沙发椅上,开门见山地对张作霖说着,“我估摸着大帅在天津。”
“翰林有什么指教?”张作霖谦恭地问着。
中国的军阀,到底也是礼乐之邦的武夫,无论他们多凶,多浑,但他们在读书人面前不敢轻慢,因为他们知道,在中国,不先把读书人买通了,就休想坐收天下。中国的读书人没能耐,但是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,读书人一瞎搅和,必把天下搅得一塌胡涂。所以无论哪一派系的军阀,尽管他们一面杀共产党,可同时他们还要作出一副姿态,把几个老学问篓子当圣人一般地供奉着,以此表示王道。
“我想,大帅此番来津,必是为了和阎锡山的战事吧?”布翰林察看着张作霖的面色问着。
“翰林圣明。雁北打起来了。”
“莽撞,莽撞。”布翰林双手拍着沙发椅靠手说着,“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,你看看这篇文章。”说着,布翰林从怀里取出一张《庸言》报,这是他从无非子相室带出来的。
张作霖莫明其妙地接过报纸,布翰林帮他展开报纸,指着一小段文字给他看。张作霖虚合着眼睛看看报纸,那上面的标题是:雨亭遇柴堡,大将军不畏地名乎?
“什么意思?”张作霖抬头问道。
“雨亭是大帅的大号,柴猪堡或可称作柴堡,自古大将忌地名,雨亭,柴堡,你不以为这地名不吉吗?”
“还有一个猪字。”张作霖刚刚拿下柴猪堡,自然不服,他争辩地大声说着。
“就在这一个猪字上呀!”布翰林一挥手,激动地站起身来,“张大帅生于光绪元年,光绪元年是公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,是年的干支是乙亥。大帅你属猪!”
“啊!”张作霖吃惊地吸一口凉气。
布翰林顺势又走上一步,对着张作霖大声说道:“今年大帅四十八岁,又是本近年。”
“啊!”张作霖又是一声惊叹。
“张雨亭生于乙亥,四十八岁上,又逢亥年,偏偏要去攻打柴猪堡,莫非你忘了要三思而后行的至理名言了吗?”
“翰林赶紧找人给我相面算命吧。”张作霖气馁地说着,“听说天津有个无非子……”
“他躲起来了。”布翰林又坐了下来,万般无奈地说,“我本来还疑惑,他躲的是哪一个?如今明白了,他躲的就是你张大帅呀,无非子,你真是神仙呀!”
九、
住在聚合成饭庄的一套客房里,无非子将一个斗大的“进”字,写在一张一丈二的宣纸上,悬挂在墙壁上,每日坐在这个“进”字的对面,仔细端详。只是要说清楚,尽管习惯上手写体的‘进’字已经有了好几种写法,但无非子规规矩矩写的是正体:進。
只有宋四妹能和他说贴心话,她见无非子每日冲着这个“进”字发呆,便好奇地问着:“你犯的哪家子神经病?不就是一个字吗,还能看出个大美人来?”
无非子不理睬宋四妹的奚落,仍呆瞧着这个“进”字回答说:“这个‘进’字将我绊倒了,我还得扶着这个‘进’字站起来。”
袁军长离津一个月,消息传来,如今已是威震一方的人物。原来游窜在陕、晋一带地方的几个旅,穷得开不出军饷,靠掏老百姓的鸡窝过日子,袁军长财大气粗,一股脑买过来,收编成什么师什么旅什么团,发新军衣买新枪炮添置军车,没几天工夫便折腾出一派非凡的气势。再加上天津有《庸言》报,北京有《神州报》添枝加叶一阵吹嘘,连正在北伐路上的国民军都估摸着山西、陕西一带的袁将军不是个好对付的人物。恰好这时,说来也怪,张作霖突然由柴猪堡前线调回兵马,未及月余,柴猪堡几乎变成一座空城了。于是袁军长长躯直入,一时间柴猪堡大军压境,荣军长已经向张大帅再三告急了。
无非子给袁军长断的这个“进”字,又成了子平学界的一大佳话,《庸言》报上几篇文章吹捧无非子料事如神,他居然给一个被杀得片甲不留的败将批了一个“进”字,就是由这一个“进”字,这个败将时来运转又成了气候,无非子下一步就要给民国政府卜测吉凶了。
袁军长收复柴猪堡,已成定局,不出十天,捷报就要传来,因为无非子嘱咐过袁军长,四十天之内不可用兵,所以前线上袁军长憋足了一口气,准备一举成功。张作霖这边,终于布翰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无非子,无非子料定四十天之内柴猪堡尚且天地交泰,不会有突降的灾难。但在七七之后,火王星南移,此时金星暗淡,水星无光,张大帅不宜用兵,倘此时柴猪堡有战事,请张大帅好自为之。百日之后,火王星下沉,金星突亮,水星高升中天,那时日有紫气起东北,亘西南;夜有赤星自西南人,其光烛地,该正是秋风爽战马肥士卒勇,莫说是一个小小的柴猪堡,只怕大半个中国都要非张大帅莫属了。
“袁军长一旦收复柴猪堡,他决不能慢待你,狠狠敲他一竹杠,咱俩远走高飞算了。”宋四妹终归是妇人之见,只盼着无非子能发笔小财,俩人躲到什么地方过小日子享福去。
“早以先我也曾这样想过,那时我性命难保,只盼着能闯过这道‘坎儿’,再不吃江湖饭了。”无非子燃上一支烟,细细地品着味道说着,“可住在这客房里审时度势,我看出这中国的压轴戏还在后头呢,一个小小的袁军长掀不起三尺的浪头,我只吃他一口饭便洗手不干,岂不是太冤枉了吗?你看当今之势,七十二路诸侯大起大落,鹿死谁手,谁主江山,如今还看不出来眉目。乱世出豪杰,豪杰们都是豁出一条性命碰运气,成者王侯败者贼,所以这几年相士们都发了财。我如何能眼巴巴看着这后面的一块一块肥肉让别人叨走呢?我还要干,我还要干大事业,来日说不定哪位帝王之材靠我保佑着收了天下,我,就是刘伯温了。哈哈!”无非子说到得意处,自己放声笑了起来。
……
在袁军长离津后的第四十一天,消息传来,袁军长收复柴猪堡,荣军长望风而逃,张大帅前线收兵,阎锡山犒赏袁军长,奉系军阀吃败仗了。
哈哈哈哈!
无非子相室一片喜气洋洋,无非子大摇大摆地回到了自己的相室,大把钞票拍在桌上,小神仙鬼谷生得赏银二千元,几个看相室的佣人每人二百,四间相室扩大到八间,换装上荷兰国的玻璃百穗吊灯,铺上波斯国的男工手绣地毯,宋四妹买了钻石戒指,而且几位老友也各有馈赠,刘洞门一辆新包月,左十八爷一只翡翠板指,哈哈王爷一只纯种法国鬈毛小巴狗,布翰林一部宋版《易传》。至于无非子自己得了多少钱财,外人就不得而知了。
“哈哈哈哈!”哈哈王爷自然又笑了。
无非子相室入夜又铺开麻将桌,无非子、哈哈王爷、左十八爷、刘洞门又摆开了方城之阵,布翰林因奉系军阀失势心中稍有不悦,比平日走得更早,回家品玩那部宋版《易传》去了。麻将牌桌上四个人喜笑颜开,耍得比两个月之前还要开心。
“这个姓袁的小子够义气。”哈哈王爷搓着麻将牌连连赞叹,“果然是收复了柴猪堡立即清还债务,我的股票都提出来了,他还再三问我老祖坟在什么地方,好派兵为我把守。”
“王爷。”刘洞门向着无非子笑笑,侧目对哈哈王爷说着,“你可千万别告诉他准地方呀,兵家有胜有负,当心他败时顺手牵羊。”
“我比你明白,刘爷。”哈哈王爷万分自信地说,“带兵打仗的发财,一靠抢掠搜刮,二就是靠掘人家祖坟,哪个军人不挖古墓呀,我见过的太多了。哈哈哈哈……”
“这场事可把我吓傻了。”左十八爷将一张东风拍在桌上对无非子说,“干着急,使不上劲呀。按理说聚合成饭庄就和我自己开的买卖一样,国人救人的事咱不是没经过手。可这次是军界,他妈的兵痞,不讲理的祖宗,咱这百八十个哥们儿递不上手呀!”
“十八爷帮了大忙啦。”无非子仍是万般感激地说着,“当天下午就接上了线儿。”
“没嘛,没嘛。”左十八爷得意洋洋地说,“反正这么说吧,只要在天津卫,无论是丢了东西丢了人,明道上暗道上,都瞒不过我。还记得那年英租界乔总督撞上‘高买’的事吗?从汽车走下来,左边一个随从,右边一个秘书,后边是四个保镖,过边道进家门一共不到十步远,领带上的钻石别针没了,偷的不是东西,让你见识见识世面,没两下子别来中国摆大尾巴鹰。乔总督眼了,托人求到咱爷们儿名下,我说好办,明天中午十一点,原地方给你挂上。你猜怎么着?到了第二天,乔总督挺胸站在边道上,前后左右站着暗探,他自己死盯着自己的领带。就看见马路当中有个小孩打水枪,乔总督怕溅着水珠,身子一摇晃,你猜怎么着,钻石别针又别在了领带上。打从那以后,乔总督再见到我左十八爷,远远地先抱拳作揖,这事不吹牛吧?”
“亲眼所见,亲耳所闻。”刘洞门连连答应着,说话时还翘起大拇指。
“就是跟挎枪的丘人们没法儿。”左十八爷不无遗憾地摇摇头,“唉,秀才遇见兵,有理说不清呀。”左十八爷一番叹喟,众人都觉合理,一致认为不可与兵家论纲常。
四圈麻将牌依然是打到东方破晓时刻,哈哈王爷依然是输了二百元大洋,左十八爷、刘洞门、无非子依然是各赢五十、六十、七十元不等,四个人在佣人侍候下洗过脸,和往日一样,又到了各自找各自去处的时候了。左十八爷这些日子早晨忙,正在码头上成全一笔大交易,货在船上,总找不准上岸的时辰,左十八爷已经在口儿上活动七八天了,说是三五天之内警察署放一个“冷子”,那时买卖成交,便是成千上万的好处,所以话没得说几句,左十八爷便匆匆走了。哈哈王爷天亮之前必须赶回府去诵经敬香,坐上包月车也走得没了影。相室里只还有刘洞门和无非子两个人,刘洞门神秘地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纸条交到无非子手里。
“什么?”无非子向刘洞门问道。
“电报稿。”刘洞门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“什么电报稿?”无非子莫明其妙地又问。
“奉系的荣军长撤出柴猪堡,全军兵马驻扎在古北口一带操练。”
“他当然不会回关外,好不容易给自己打出一片地盘,他还会乖乖回到张作霖眼皮下边去挟尾巴过日月?”无非子看着电报稿回答。
“所以我劝神仙兄长是不是应该躲避几日?”刘洞门一面整理衣饰一面说着。
“为什么?”
“倘若那荣军长住在古北口无聊,一高兴要来天津玩几天,那时悄找到神仙相士,这一阵报上没少张扬神仙给袁军长指点迷津的神通,万一他恼羞成怒……”
“谢谢洞门仁兄提醒,我只是怕这个荣军长不肯到相室来找我呢。哈哈!”
“怎么,你在等他?”刘洞门大吃一惊。
“洞门仁兄且看下回分解吧,我还有好生意做,主笔还有好文章写呢,哈哈哈哈。”
说笑着,无非子送刘洞门走出相室,刘洞门摸不着头脑,糊里糊涂,只得快快去了。
说来也怪,今天无非子没有去赴宋四妹公馆的约会,却回身坐到相室里,端端正正地读起了《易经》。
……
“师父,大事不好啦!”
小神仙鬼谷生去万顺成早点铺喝锅巴菜,才咬了一口烧饼,一抬头正看见天祥商场后门黑压压百多十人恶汹汹往里闯。清晨七点,天祥商场还没有开始营业,看夜打更的伙计自然要上来阻拦,没想到这些人蛮不讲理,半句话不说冲上去就动老拳。鬼谷生看了一眼,心中已觉察到凶多吉少,喷香的锅巴菜没喝一口,拔腿就往天祥商场里钻。噔噔噔急急急快如风,一口气跑进相室,才放开嗓音喊叫一声,不料却被四个大汉四只大手一齐抓住,鬼谷生才要挣扎,只觉得硬梆梆的什么家伙顶在了后腰眼儿。我的妈!鬼谷生哼了一声,早瘫成一堆烂泥,再不出声了。
呼啦啦几十个军人涌进了无非子相室,这些人一个个青面獠牙,眼睛里布满了血丝,活像是恶狼才吃了死人,为首的一个身佩武装带,腰挎着盒子炮大军刀,亮锃锃马靴地板上狠狠踹着,破口便是大骂。
“妈拉巴之(子),丫头养的什么无非子,你给我爬出来。”
声音惊天动地,满天祥商场的人都当是晴天打下了霹雳,许多人跑来围在无非子相室门外看热闹,彼此悄声猜测无非子到底惹怒了哪路的英豪?
惟有相室里没有反应,无非子明明就坐在内间相室里,莫说他平日只是装聋,就算他从生下来就是一点声音听不见,这恶汹汹一干人等扰起的恶浪也能把他打个大跟斗。偏偏他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,什么也没有感觉到,仍坐在案前读《易传》,伸出舌头舔舔手指,他还慢条斯理地翻了一页书。
当地一声,为首的那个少壮军人狠狠地踢开了内室的木门,顶天立地一只黑宝塔,这个活似狗熊挎战刀一般的豪杰站在了无非子面前。
这时,无非子才缓缓撩起眼皮,似是无心地向来人望了一眼,然后双手微微地拱在一起抱拳作了个揖,吸足一口气,方才语调平和地说道:“无非子恭候荣军长多时了。”
“你个猴小子就是无非子?”来人一巴掌拍在书案上,凑过身子,鼻子对着鼻子问着。
“不才便是。”无非子回答。
“谁给你报信说你荣爸爸今日要来?”
“出口不逊,恶语伤人,非礼也。”无非子虚合上眼睛自言自语地说着。
“来人哪!”荣军长一声喝叫,早有八个丘八拥上来,从左右两侧抓住了无非子。“把无非子这丫头养的给我押走,天津卫不是咱的地界,弄到古北口军营里我一刀一刀剐了他!”
荣军长话音未落,八个军人早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个瘦骨磷峋的无非子绑了起来。
“哈哈哈哈。”无非子一没有惊慌,二没有反抗,反而爽朗地放声笑了。
“你笑啥?”荣军长揪住无非子衣领问着。
“我笑荣军长恩将仇报,误伤了暗中助你的真人。”
“你说啥?你还是我的恩人?你暗中还助着我?亏你说得出口,那姓袁的小子让我打垮了,夹着尾巴逃到天津来,你批了他一个‘进’字,他才又招兵买马回柴猪堡跟我拚命。”
“这才是我暗中助你。他袁某人身为一介武夫,柴猪堡一箭之仇他必是怀恨在心,你虽然夺得了他的地盘,可此人一日不除,你一日不得安宁。你盘踞柴猪堡追他尚愁鞭长莫及,我让他回去自投罗网,难道不正是暗中助你吗?”
“呸!”荣军长可不是凭他无非子花言巧语能胡弄的人,“你那嘴跟屁股眼子一样,开着花地翻,你批的那‘进’字咋个解?”
“我批的这‘进’字原是劝他就此罢休,不要再跟荣军长过不去了。”
“瞎扯吧,你当我不识字?‘进’就是前进,前进?杀呀!”荣军长向无非子表演了一番冲锋陷阵的功夫,果然,这“进”便是前进。
“差矣,进者非进。”无非子被人绑住了双臂,说话时只能靠摇头摆脑表示得意。
“胡掰吧,进咋成了不进?”
“那里有纸和笔,请荣军长写个进字。”无非子支起下巴,示意给荣军长放笔墨的地方。
“写就写。”回过身来,荣军长操起笔来,在铺在案上的宣纸上写了一个“进”字,荣军长的墨宝是螃蟹体儿,但字写得横平竖直,且又是正体繁字,没有什么挑剔。
待荣军长放下毛笔,无非子又虚合上眼睛,似平日批命相面时那样操着抑扬顿挫的语调说着:“这‘進’字,上面是个佳字,外面是个走字,我明明告诉他三十六计走为上,他偏偏以为是我让他进军发兵收复地盘。是我无非子批错了命相,还是他不识我无非子的真言呢?”
“啊?”荣军长呆了,他一双手插在腰间,冲着自己写的那个“進”字端详了半天,他越看越觉得无非子说得有理,越看越觉得这个“進”字原来就是以走为佳的缩写。“三十六计,走为上?来人哪,给神仙松绑!”
七手八脚一阵黑旋风卷过去,无非子又端起了神仙架势,他整理好长袍马褂,将被绳儿系着皱巴巴的衣袖舒展平整,重新在太师椅上坐好,摇头摆脑地说道:“既然求问神明,就当深思神明的指点,袁军长一介鲁莽,得了一个‘进’字便以为吉星高照,所向披靡了。其实他根本不知道‘进’字作何解释。”无非子说着话将一双胳膊举起来,让长袖褪至肘间,露出一双手背上暴着青筋的大手,比比划划地说下去。“君子之‘进’,君子进德修业,他袁某人刚刚被杀了个落花流水,即使不是天意灭你,你也当暂且偃旗息鼓,进业修德,思想自己何以失德失道失助失时失势,进而悟彻作人的道理,从今后知天命守本份,再不可有份外之念。这个‘进’字,不正是劝他不可轻举妄动吗?而且,进者,尽也,《列子·黄帝篇》有言,‘竭聪明,进智力’,此所谓聪明、智力已经竭尽了,从此不能再成大业。更何况进退维谷也是‘进’,进寸退尺也是‘进’,偏偏他袁某人只将个‘进’字当作是率兵出征,他不明明是自找身败名裂吗?”无非子越说越得意,他已经将一个“进”字解得全无进意了。
“神仙圣明。”荣军长终于心悦诚服了。他立即向着无非子立正站好,一双马靴重重地撞了一下靴子后跟,清脆一声响,荣军长向无非子致了个军礼。“神仙别和我一般见识,只当我是个粗鲁人,刚才犯混脾气,神仙多包涵。您老若是觉着不出气呢,就拥我两个大耳光之(子)。”不等无非子动手,荣军长先抡起巴掌拍了自己两记耳光,看看无非子似是消了气,荣军长才又说道:“不管怎么说,我算是让姓袁的撵出来了,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?”
“如此又是荣军长多虑了。”无非子活动着刚刚被绳儿勒疼的手腕,慢慢说着,“当初荣军长强攻柴猪堡,杀得袁军长丢盔弃甲,最后他只身逃到天津,八方筹措才借到军款,这才又收买下散兵游勇重回柴猪堡;而荣军长放弃柴猪堡未伤一兵一卒,只是张大帅忌星相赵易,这才调虎离山,以荣军长的兵力……”无非子话到唇边不说了,这时鬼谷生献上茶来,无非子抿一口清茶,算是驱散刚才的一阵晦气。
“有话,神仙只管说,拿回柴猪堡,我给神仙打一百个金嘎子。”
“既然张大帅有令调荣军长出关……”无非子莫测高深地故意挑逗。
“嗐,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呀!我咋不杀回去呢?神仙,你快给我算一卦吧。”
“算完了。”无非子收拾案上的纸笔,看也不看荣军长一眼,只向门外招呼:“送客!”
“啊?!”荣军长呆了,“这就是算完了?好歹神仙也得批我个字呀!”
“你自己刚才不是说出那个字了吗?”无非子向荣军长反问着。
“我说啥了?”荣军长寻思好久,终于他还是想了起来,“我说了一个‘回’字。”
“你把这‘回’字写下。”无非子又补充一句。
荣军长立即在纸上写了个“回”字,写好后,他呆望了一会儿,心领神会地说着:“神仙的心意我明白了,这次我杀回柴猪堡,要把柴猪堡里面设一个包围圈,外面再设一个包围圈。上次我吃亏就在只围了三面,给姓袁的留了一条逃路,这才给自己留下了后患。这次我大圈紧,小圈缩,给姓袁的来个全军覆没,活捉住姓袁的,杀头祭刀。”
“送客!”无非子又说了一声,然后便劳累万般地颓然坐下,再不说一个字了zy0123。
“谢谢神仙。”荣军长只得告辞了,走到门外他返身对无非子说,“今日先送神仙两千元大洋压惊,来日必有重谢。中国风水大师风水学趙易整理本资料”
“送客……”












 位浏览者
位浏览者